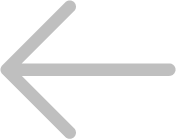[ 轻清江南 ]
王辉
/
江南不仅仅是指地域,更是一种地域气质。建筑中的江南早已被当前急剧的城市化蚕食殆尽。因此,能在江南看到渗透着江南气息的建筑,很会令人兴奋。大舍事务所新近完工的嘉定新城幼儿园,就是这样一则案例。几年前,我曾以《轻与清》为题,借青浦私企俱乐部项目,写过他们笔调轻松、思路清晰的特点。[1]这种需要在慢中品尝的轻与清,是一种放松,以及在这种放松中对设计本质性问题的深刻把握。轻与清属于江南的一种品性,在这个慌忙的时代,久违了。
嘉定新城幼儿园之所以有这种江南品性,在于大舍先给自己拟了一道不好解的题,再用一种放松的方式把答案解出。幼儿园本应是轻巧的项目,常例是把体量作碎、作小、作轻,例如大舍的青浦夏雨幼儿园。这个建筑却敢把体量做整、做大、做重,将整个建筑整合为南北两个同高的体量:北侧是交通空间,南侧是15个班级的教学用房。比起处理成高低错落、大小有致,这种手法在建筑的轮廓线上没有优势。大舍却巧妙地运用了两个体量之间的对话,在本是无聊的长方形轮廓内,聊出了一段恋人般的缠绵絮语,并让观者在慢慢细读中,品出其中三味。
这个对话源于南北两个体量清楚的组合之中,又有一丝悬念。面向街道的北墙几乎突兀无窗,显示出刚和实;南墙开着密密麻麻的窗,却隐没在穿孔瓦楞铝板后面,显示出柔和虚。两个体量都沿着呈W型的路径微折,使刚而不僵,柔而不软,线条比较有韵味,算是对直白的外轮廓线的一种微妙的修正。刚柔、虚实对比是种拟人的做法,诱人去读出两者之间的玄妙。这个阅读,让我联想到十字架与基督这对体量,他们也是在对比之中,展示了一种艺术化的魅力:把一个受难主题(crucifixion),从物质性的沉重中放松出来,解脱为精神上的审美享受,读起来很轻。
做这风马牛不相及的类比分析,只着眼在它们各自处理一对体量的艺术手法,无关乎任何文化暗示。先拟三个命题来分析这种由重变轻的逻辑演绎:锚固中的失重;拥抱中的失重;以及映射中的失重。
命题一:锚固中的失重。基督失去了地的支撑,成了十字架的俘虏。因为重力会使基督的身体下坠,变得丑陋。艺术家只能弱化重力,强化十字架的锚固力。这种锚固是通过在心脏、双手、双脚上的五个洞口,即“耶稣五伤”。事实上,只依靠这五个洞口的锚固,基督的身躯会扭曲变形。但由于汩汩流血的洞口被描绘得生动,撩人心弦,使观者忘记了重力对基督的作用,而专注于十字架对基督的锚固。
幼儿园南墙完全被打孔板遮满,只在墙体的折角处,留着七、八个巨大的洞口。洞口成了南立面最突出的元素,通过它们,可以靠视觉从正立面沟通南北两个体块。因此它们可以被理解成两个体块间的锚固点。虽然南侧体块的重量是被地面承托,但穿孔挂板不落地,使整个体块似被轻轻抬起,通过有力的锚固,挂到北侧的体块上。洞口的视觉冲击力强化了这种锚固的力量。第一,由于两个对接面的水平楼板是错位的,洞口的水平轮廓线处生成了错层。相比于平面和屋面纤美微折的轮廓线,这种瞬间的剪切产生的几何错位,仿佛“咯噔”一声,让洞口的轮廓线响亮有力。第二,作为洞口底衬的北侧体块,是一面砖红色实墙,被从两个体量罅隙间透来的阳光照得鲜亮,使洞口的阴面被这片亮面对照得更分明,也强化了洞口的轮廓线。第三,大舍敏感地选择了不同色系的小号玻璃马赛克作为侧壁材料,使洞口变得精美和鲜活,墙面令人亲近。第四,洞口最有力的一点是,它们在二维的立面上形成了数个三维的凹入空间,即大舍所谓的沿垂直方向展开的“庭院”,使幼儿在“庭院”里的活动也成为建筑立面的一部分。这种被刻意设计的洞口,形成了南北两侧体块之间“空手道”似的锚固,使南侧体块的份量轻得像表皮的那层穿孔板。
命题二:拥抱中的失重。受难的主题本应让基督与十字架都很沉重,但二者的形体都被艺术家处理得优雅:十字架不再是粗糙曲折的原始树干,而变成优美刚直的几何体,来衬托基督躯体雅致的弱;基督孱弱得失去了重量,像天使优雅地展开双翼,柔软地躺在十字架的拥抱中。两个体量放弃了重力和十字架束缚力之间的痛苦较量,而变成一种美丽而玄妙的并置。
大舍在做设计时,虽然不会有这种联想,但他们也相似地使用了以弱来产生美感的策略,将幼儿园南北两个同构的体量处理成柔与刚的两种性格。按柯布的说法,建筑玩的就是那种在阳光下的体量的表现。南侧是受光面,本应体积感强。而大舍偏偏用微妙的几何折线、面纱般的打孔板,来弱化在强光下的建筑体块所能呈现的坚实感,反而把坚实感赋与了北面那个堡垒般的体块。对于两个并置的体块,对比是为了将二者分离,但刚柔对比,又是为了让两个体量更好地相互拥抱在一起。离是为了合。柳亦春在《离,美学及其它》中意识到,“离合作用形成的组织结构就是重叠并置,这说明物与物之间通过并置关系可以形成丰富且玄妙的动变组合。” [2]在这种组合中,假如没有弱,也没有拥抱的动力,更没有拥抱的诗意。陈屹峰在《弱秩序》一文中,进一步把这种离合中的相互拥有冠名为“弱秩序”:“弱秩序空间体系的意义同时来自于组成整体的各空间本身、各空间之间的关联与分离,以及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整体,这样形成的意义具有多义的、含混的、不确定的乃至通俗的意味,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更是对现代主义建筑一贯追求合乎理性、讲求真实与明确,力求避免含糊性和不准确性的一种反思。这种对单一、明确的挑战,最终将给建筑带来的是淡淡的诗意。”[3]通过并置的两个离合体块之间微妙的缠绵,来产生“淡淡的诗意”,与基督失重在十字架上所产生的美感,是同出一辙的。
命题三:映射中的失重。十字架本是恐怖的刑具,令人憎恶。却因拥抱过基督,反而成为基督的象征物,成为一种玄妙的美丽。基督是可理解的具象。而十字架是不可知的抽象。在基督受难前,它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寓意;而有了受难,它又忽然变成最有文化暗喻的图式。从这个意义上,每一幅关于受难的圣像画,都藏着画家的一个秘密。它可以告诉你基督的表情,却把这种表情的寓意隐藏在十字架的抽象几何学中。十字架和基督之间有着某种信息的映射。基督最终离开了,他把所有的重量都映射给了十字架。
同样,在嘉定新城幼儿园的构图中,南侧体块所要讲述的内容,虽然一目了然,但就像它表皮的面纱,总有一层神秘的寓意,诱人去想是否可以在北侧的那个封闭的体积里去寻找答案。北侧愈是封闭,这种寓意愈是婉约。在这个意义上,从南侧那些洞口中透出的北侧体块的南立面,被处理成鲜艳的实墙,而不是用玻璃墙来透视北面体块的内部空间,是绝妙的一笔。这种处理,守住了南侧故事的谜底,于是产生了一种意境。这种由藏而生的意境是大舍所欣赏的,陈屹峰说:“意境所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审美结构:一方面,创作者不希望直致其情,而将情蕴含在言中;另一方面,欣赏者则需要在言外妙会。”[4]用确定的元素去映射不确定的元素,进而又用不确定的元素模糊确定的元素,才是映射的目的。
失重是一种去物质化的动机,指向更精神化的目的。上文借用基督-十字架这则母题,来分析嘉定新城幼儿园外部空间构成中的一条清晰的逻辑。清晰并不等于清澈见底,而是提供了一条更明晰的线索,诱人慢速走到谜的深处。外部空间两个体量外在的关系,留给读者的是其内在的关联这个谜,需要到内部空间去继续寻找。
先描述一下如何进入内部空间。这是一处妙笔。建筑的主入口位于北面,被处理成一条轻轻地脱离开地面的V字型折廊,外罩和南墙一样的瓦楞穿孔铝板。我第一次造访这个建筑时,因建筑还未验收,吃了个闭门羹,但这个门廊却给了我许多愉悦。浮起的门廊的封闭性使之与日常的地有了些距离,可以滋生好奇的陌生感。从廊道的一头入,又从另一头斜插入廊子的坡道中出,仿佛已经穿过了这个房子。因为有了对外部空间的理解,如此反复走了几遭,倒是不舍得去试推大门,生怕揭穿内部空间的谜底,反而丢了胃口。保持着一种心情来,保持着一种心情去,这种体验颇有些魏晋风采。
第二次去看这个建筑时,得缘入门,而入门的体验可以用“堕入”二字。门廊虽是被夸张,但门厅并不大,就在无意一转之间,忽然堕入了一个尺度高大的大厅,即北侧那个神秘的空间。光线是从顶上的密肋梁间洒下,明亮且柔和。还未及仔细弄清空间里的元素及其关系,脚已不自觉地走上了绕来绕去的坡道。完全被无形的力量拉着我走来走去,尤如在南方古镇中穿行,毫无目的,也毫不疲倦。有趣的是,这些坡道的设计本来是理性的,因为它们是为了某个标高上的某道门而设计。但当你走上这绵延的坡道时,可能会错过这个标高,错过这道门。这种忘却,也与北侧体量的封闭性有关。假如朝南的墙面是大面积的落地窗,会更引诱人离开这个空间,走到教室。于是便要设问:为什么要这么快进教室这道门呢?孩子们都有在幼儿园门口闹别扭的时候,坡道成了入门前能解决这种别扭的过渡空间。在一个习惯了最短直线距离的时代,在一个被考勤打卡机蹂躏的世界,被拉长了的入门距离和时间成了种带罪的享受,甚至滋生出诗意。大舍用“这是一个被刻意放大了的空间体验,它揭示了这幢建筑所有与众不同之处的根源”,来描述这个空间。它可以是放大了的狮子林中的假山,或是放大了的江南小巷,或是放大了的儿童游戏场中的器械,当然,更是放大了的时间。这种水平展开的行走,可以用中国画的手卷来类比,它没有时间,或者说是种消磨时间的方式。由于水平长卷无法一目了然地读到所有内容,展开的部分又很随机,因此阅读时停顿的节奏不同,所欣赏到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这使得任何一种停顿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此情此景都能生成新的内容。由于时间的放大,在画中有了人介入的空间,以及人的心情介入的空间。同样,放大了的入门的必经之路也放大了时间,让“慢”来颠倒这个快节奏社会的一系列约定俗成。大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电梯把自己快速地抛到办公室,孩子们又何必如此呢?米兰·昆德拉问:“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了?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5]
针对当代的“快”,这种“慢”唤起了怀旧,使人呼吸到被当代速生都市窒息了的那种江南的慢慢的空气。慢,需要形式上的依托,曲折、蜿蜒、起伏、迂回、缠绵,都可以拥抱慢。因此也不难理解我们在建筑外部看到的两个体量上的种种表象,甚至连光进入这两个体量时,都要通过打孔板的过滤、密肋梁的反射,放慢速度。由于要走完正常层高所需的坡道长度太长,大舍大胆地使用了半层高,于是在立面上产生了楼板的错层,以及由此而来的那些错位的洞口。错层也带来了地面的慢。“慢”似乎也解释了南立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窗。初读这种时尚的处理方法,觉得设计过度反倒害了这个建筑。体会到“慢”这层含义时,又颇觉合适。太规则的窗使窗外的世界变得单一,失去了想象的余地。而大小不一的窗,也许会让小朋友把对世界不同的遐想附在不同的窗口。还有那些锚固两个体量的洞口,那些散布到立面上的“庭院”,也像是来自内部的这种“慢”在慢慢地通过建筑的皮肤蒸发到空气中。
当北侧体量所隐藏的谜底昭然时,我们也理解了大舍在项目说明中提到的,“它揭示了这幢建筑所有与众不同之处的根源”。回到对两个体量的外部特征的分析,会发现所有的元素都在清晰地围绕着设计理念,并轻松地逐层剥开这一理念。那三重失重与慢的关系也清晰了。通过锚固和拥抱,南北两个体量在两者相互拥有的关系中,弱化了物质感,进而通过映射,让建筑从直白的、物质化的解读中彻底超脱,而进入了一层更神秘的阅读。解开这条失重的线索,需要时间,需要在慢中打开这个建筑。这是一种需要精神领悟力的放松中的解读,解读中的放松。之如江南的画意,是美在文人的诗情之中。
在一个速生城市的时代,建筑通常清得发白,轻得发飘。在这种背景下,大舍设计中的慢,倒也不是啰嗦,而是在一个清晰理念下的深度展开。这是深思熟虑后的简约洗练,显出一种有醇香的清,和有重量的轻。虽然他们的设计语言是西式的现代主义,但透露着与麻木的快速都市化对立的那种情感丰富的江南气息。当建筑的物质外壳里的精髓被时代彻底置换时,人们对江南的怀旧更不趋于形式,而趋于对感受的一种记忆。记忆的是情调,而任何形式语言似乎都可以唤起这种情调。之如柳亦春所说:“我们是否可以——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或者,简单地说——重构我们心底的江南?”[6]
/
[1] 王辉,《轻与清》,《建筑师》,2006/8期,
[2] 柳亦春,《离,美学及其它》
[3] 陈屹峰,《弱秩序》
[4] 陈屹峰,《弱秩序》
[5] 米兰·昆德拉,《慢》,上海译文出版社,p3
[6] 柳亦春,《离,美学及其它》